第二十五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正式开赛
由中国侨联、全国台联、人民日报海外版、《快乐作文》杂志共同主办的第二十五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于近日正式发布征稿启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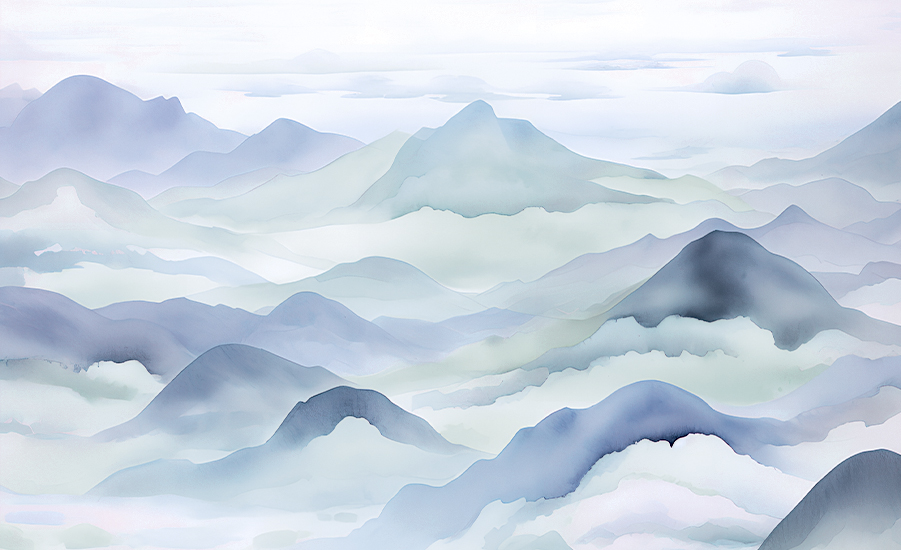
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由中国侨联、全国台联、人民日报海外版、《快乐作文》杂志共同主办, 迄今已成功举办二十四届。参赛对象为中国内地(大陆)高中在校学生,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地区18周岁及以下青少年学生,海外各国、各地区18周岁及以下华裔青少年学生。大赛已列入教育部2022—2025学年全国性竞赛名单之中(公示文件为《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2022—2025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的通知》(教监管厅函〔2022〕13号))。
大赛自创办至今,得到了海内外师生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参赛学生覆盖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子女,参赛人数累计达到数千万人次。大赛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已经成为联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一个重要载体。

2024.11.1~12.31
2025.1.1~2025.2.28
2025.3.1~2025.3.31
2025.4
2025.7